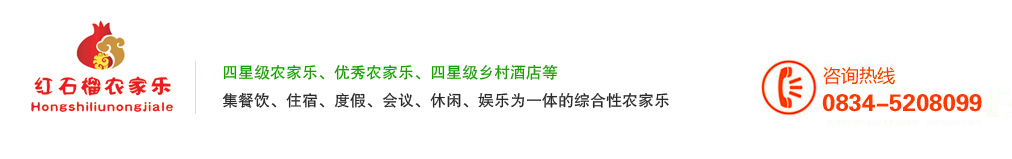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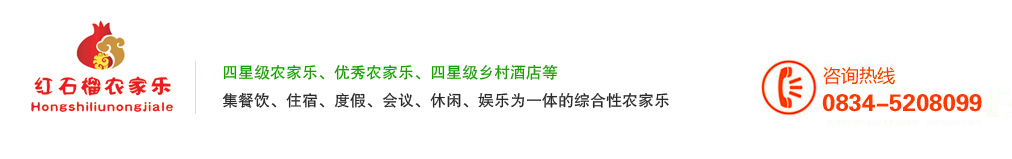
三月的成都平原,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开了,农家房前屋后的桃花李花也开了。黛瓦白墙的川西民居掩映在一簇簇树丛、竹林中,外乡人也难免被勾起乡愁。

在川西的一座老屋里,大学毕业生罗丹正操着针线缝制一件雪白的T恤,准备下缸扎染。在成都工作数年,走遍了国内很多地方,今年春节后,她决定回到村里,“一直渴望有多好的机会,多大的平台,才知道自己渴望的原来就是故乡自然质朴的生活。”
老屋的租客是一位名叫宁远的主持人、作家、服装设计师。她和合伙人画家寒山在这里开起了草木染工作室,罗丹正是和他们一起工作。
蒲江县甘溪镇明月村,这个靠着老318国道、在成雅高速通车后一度被冷落的小村庄,曾是成都市最偏远落后的村,现在却成了艺术家的乐土,勾起了很多人的乡愁。
微信朋友圈里,大家既惊讶、又羡慕地评价罗丹“过的是陶渊明式的生活”。
归园田居,源于成都市“小组微生”的新村规划理念。“小组微生”,即小规模、组团化、微田园、生态化,不搞“一个样、一展齐、一般高”的新村,成都要让农房好似“从大地里生长出来”一样。
去年12月,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在全国推行乡村规划,提出到2020年,全国所有县(市)要全面完成县域乡村建设规划编制或修编,实现乡村建设发展有目标、重要建设项目有安排、生态环境有管控、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有保护、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有措施。
乡村规划,如何规划乡村?乡村往何处去?成都的一些实践,颇能给人一些启示。

“半截子”老村来了40位艺术家
这个生长雷竹、茶园、保留着“四川最后一座活着的邛窑”的地方,好像一下子勾起了很多人的乡愁。公益组织来了,乡村规划志愿者来了,农民似乎也“觉悟”了,他们把堆在角落的瓶瓶罐罐亮了出来,把前院后坝清理出来,开起了农家乐。
竹林、幽径、柴扉、染布姑娘,这诗歌中的画面,现实存在于成都的老村中。3月11日,记者从成都市区驱车1小时来到蒲江县甘溪镇明月村。
这座染布的老屋,是川西林盘上一座典型的宅院。林盘,是成都平原上特有、具有全国唯一性的聚落形态,少则几户、多则几十户人家把房子建在一起,周围种植高大乔木和竹林,抱团抵御平原上无遮无挡的风。房子随坡就势,朝向各异,往往有水系穿过,出门就是农田,集生产、生活和景观于一体,天人合一。
经过宁远和寒山两人的改造,老屋装了地暖,开了几个小天窗,但土墙木梁、大缸小罐都保留了下来,就连原来的猪圈也改造成了工作室。
穿过竹林里的T台,高高的晒布木架,寒山黑衣飘飘、两手靛青地进了院子,向我们和院里的几位访客问好。
现在,像宁远、寒山这样的“新村民”,村里来了40来位,带来了30个文创项目,有陶瓷工坊、艺术酒店、茶社、画室、篆刻传习所等,村里访客不断。
这个生长雷竹、茶园、保留着“四川最后一座活着的邛窑”的地方,好像一下子勾起了很多人的乡愁。公益组织“3+2读书荟”来了,乡村规划志愿者来了,农民似乎也“觉悟”了,他们把堆在角落的瓶瓶罐罐亮了出来,把前院后坝清理出来,开起了农家乐。政府和乡村规划师帮他们把后建的水泥房子用黄泥掺麦秸、竹木草等乡土材料修饰起来;就连村里的垃圾桶,都是扁担和木桶,一只写“可回收”、一只写“不可回收”。
在明月村,新老村民开始了奇妙的互动。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清租下一件老屋,开办了瓷板画创作室“蜀山小筑”,邻家村民吴耀锦马上开起了农家饭店,他30岁的女儿吴蕾每天从邻村跑回家帮忙。“以前的生活那么平淡无味,现在,整天看他们做陶器、弹琴、画画,我也想跟他们学学了!”她说。
“我们可以教村里的小孩捏泥人,带着青年编斗篷、编蓑衣;可以开发精美的茶叶罐,装着农民的茶叶一起卖;还可以把瓷板画镶在村民打的竹桌子、竹椅子里,形成新的产品。”李清的画家朋友刘以佳说。
318国道旁边的一处石头房子,是明月村的游客接待中心、甘溪镇文化站,也是新老村民集中交流的场所。
图书室管理员郭晓岚身着制服,举止优雅,她是去年11月开馆时招聘的村民。她指着一张排得满满的日程表告诉我们,每周末,这里都开设艺术家对村民的“明月讲堂”,会议室装不下,就转移到阅览室;阅览室还装不下,村民就站到门外。每两周,在村的艺术家会来这里义务地教留守儿童书法、绘画、做手工。
遗憾的是,因为前几年搞集中居住,老村的老屋拆得只剩下了1/3,成了“半截子”老村。艺术家们涌向明月村,县里又用该村集中居住节约的187亩建设用地,在明月村新建了一处“核心区”,分成17块小地,很快被艺术家们签约一空。

新居为什么要那么多卫生间
规划院和乡村规划师还建议,新居的每个卧室都要带卫生间,村民不理解:要那么多卫生间干什么?白占地方。现在,村民告诉外来的参观者:这是经验!游客来了,一套卧室就是一套客房。
和明月老村的幽静不同,郫县三道堰镇青杠树村是一个入住只有3年的新村,看起来也热闹得多。3月14日并非周末,村里却挤满了赏花、钓鱼、喝茶、打麻将的人群。
邓薇是2010年成都市第一批统一招考的乡村规划师,她亲身参与了青杠树村的规划建设。她说,该村三面环水,渠系纵横、林盘众多,柏条河与徐堰河在村头合流为府河,是成都的水源河。2012年,三道堰镇政府提出,有这么好的资源,农民愿不愿意搞新农村建设?
90%的人表示同意。但怎么规划?村民意见不一。有的提出进镇集中居住;更多的人想聚集到成都连接郫县的干道——沙西线两边去,夹道建设,开店赚钱。镇政府、规划院、乡村规划师则建议保留一些原有林盘,适度散居,不要远离原有的生态资源,可以搞产业。
“村民采纳了建议。但一部分村民还是愿意留在路南,就形成了现在路南4个、路北5个组团的格局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旅游区,正是路北的几个组团。”邓薇说。
设计房子时,也讨论了多轮。邓薇说,最初规划设想是人均建筑面积35平米,多节点地,指标卖钱搞配套;村民觉得太挤,调整到了45平米。村民觉得房子越大越好,恨不得把宅基地全部建成房子,盖成3层;而乡村规划师提出,要留出庭院,房屋立面要凸凹有致,除了5人户局部建成3层,大部分房屋不超过2层。这一点,村民同意了。
规划院和乡村规划师还建议,新居的每个卧室都要带卫生间,村民不理解:要那么多卫生间干什么?白占地方。现在,村民告诉外来的参观者:这是经验!游客来了,一套卧室就是一套客房。
对不愿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村民也并不强迫。青杠树村的6号、7号组团边上,记者看到,几户村民还住着原来的老院子。邓薇说,青杠树村的参与度97%,已经算很高了。
启动新村建设,青杠树村用的是“农民集中建房小拆项目”政策,由村民成立土地合作社自己运作的。邓薇说,自主运作的结果就是积极性高,村民2012年6月18日开始报名,2013年7月就分房了,800多户人家,只用了短短1年时间。
而离青杠树村不远的程家船村,是社会资金进村运作,村民总有一种“被占便宜”的感觉,好几年了,参与率还不超过80%。
青杠树村的农居没有围墙,家家户户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间开起了茶馆、餐厅、棋牌室、小卖店,有人还出租自行车、卖干菜、竹编等土产。村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,现在,青杠树村年接待游客100万人次,年旅游收入3000万元,正在申请4A级景区。2012年,青杠树村村民的人均纯收入是11953元,而2015年变成了18300元。

不搞“排排坐”,要“小组微生”
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。在成都,规划师们形成了一个共识:城市应该更像城市,农村就该更像农村,“我们不搞‘一个样、一展齐、一般高’的新村,要让房子好似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一样”
3月10日,我们来到成都彭州市濛阳镇青江村。濛阳是西南重要的大地蔬菜产地和集散地,人称“北有寿光、南有濛阳”。从路边远看,新村白墙黛瓦,坡屋面、木穿斗,高低错落,清丽如画。进村一看,房屋简朴又讲究,每栋楼的高矮胖瘦都不一样;再看细部,仅是屋脊的镂空拼瓦,就有鱼鳞状、人字状、平行状,相邻的几栋楼各不相同。
“一人户是1层,二、三、四人户是2层小楼,五人户是3层小楼;拼在一起,有‘1+2+2+1’、‘3+3+2’等各种组合,就错落开了嘛。”从彭州规划局挂职濛阳镇副镇长的何林徽“揭秘”。
28号楼户主、47岁的村民钟季音自告奋勇地请我们到她家里看看。她家离村口不远,弯弯的道路入口竖着一个木门楼,上书“映合居”。这是他们原有村民小组几十户组成的组团,和别的组团之间用菜地相隔,彼此联通,又相对独立。
钟季音家是3人户,建筑面积120平米,和南侧、东侧的房屋围合成了个小院落。她在房前屋后的小菜园里种了香菜、小葱、莴笋和豌豆尖,还在门口拴了一只毛色光亮的大公鸡。
一看青江村搞得好,邻村白土河村的村民也心动了。这个村是川剧大师阳友鹤的故乡,成都市规划局直接为其规划方案把关,准备把它打造成川剧名村。继这两个村之后,整个蔬香大道沿线村庄都要统筹规划。
国务院参事、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曾说过,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。在成都,规划师们形成了一个共识:城市应该更像城市,农村就该更像农村。
记者了解到,成都市也曾搞过“三个集中”,汶川地震后重建也曾简单模仿城市,盖起了一些“排排坐”的村庄。但2012年以后,成都提出“小组微生”的新村规划理念,新村的风貌大变。
“小组微生”,即小规模、组团化、微田园、生态化。成都出了专门导则,新村规模一般100户至300户;内部每个小组团20至30户,一般不超过50户。绿化不搞行道树、冬青、月季,而是房前屋后种果种菜。老村的田水路林尽量不动,保护林盘、田园和农耕文化,体现背山、面水、进林盘的乡土味道和农村特点。
“我们不搞‘一个样、一展齐、一般高’的新村,要让房子好似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一样。”成都市规划局副局长张佳说。
成都市规划部门调研发现,过去他们对一些新型社区的弹性设计不够,不能很好地适应其下一步产业升级发展要求。最近有个村,几户老百姓有9套房子,空出来,就是一个小型的酒店。这对他们的启发是,下一步,应该在村庄预留一些弹性空间。
不断总结的结果,是成都出台了一系列“农村红皮书”,包括《成都市城镇及村庄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、《成都市村庄规划编制办法》等一系列技术规定、导则和地方标准,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规范标准体系。今年,成都市规划部门还打算出成方连片村庄的规划导则。

年薪10万,乡村规划师有一票否决权
五星村的新村道路规划时准备留6米宽,太窄了跑不开车,但6米宽又容易在视觉上破坏乡村的尺度。宋永星建议,道路还是留6米宽,其中4.5米用水泥硬化,另1.5米用青砖铺装。
在成都,还有一种特有的职业:乡村规划师。他们是成都市规划局筛选、招募的专业技术人员,他们对乡村规划有热情,职责是乡村规划的决策者、规划初审把关人,还是实施过程的监督员。外界报道他们,年薪10万元,有一票否决权。
31岁的安徽小伙宋永星去年从成都一家国有设计院辞职,考取了乡村规划师,来到白头镇,一头扎进了建设中的五星村。当时,五星村的建筑主体已经完工,正在做景观。学建筑设计专业的他,愣是从头学起了景观设计。
“乡镇的规划力量非常薄弱,学规划专业的大学生很少来到乡镇。而设计院又不了解乡镇,如何把镇里的规划意图落到地上?乡村规划师这个专业人士帮了大忙。”当着宋永星的面,崇州市白头镇五星村镇长黄荣夸赞他。
记者获悉了一个细节,五星村的新村道路规划时准备留6米宽,太窄了跑不开车,但6米宽又容易在视觉上破坏乡村的尺度。宋永星建议,道路还是留6米宽,其中4.5米用水泥硬化,另1.5米用青砖铺装。记者在村里看到,这样一来,村路还是保持了“蜿蜒小径”的风貌,同时兼具了交通功能。
规划落实到不到位,宋永星在现场盯着。在成蒲铁路安置小区,建筑队把房屋外立面的腰线砌得齐边齐沿,整齐有余,韵味不足。宋永星和镇里分管规划的副镇长易惰在现场盯着,一堵墙一堵墙地支招,这里出个垛头,那里拼个砖花,总算漂亮了起来。
在明月村,30岁的乡村规划师邓小玲正在和一个村民“较劲”。 这个村民看村里游客多了,就将自己的老屋扒了,准备建一座3层楼接待游客。但是,新建房屋要符合老村风貌,按规划导则也不能超过2层,邓小玲驳回了他的图纸。村民直接找到了县规划局,规划局明确表示按导则来。
在三道堰镇,乡村规划师邓薇在镇总规编制过程中,提出了重要的建议。本来镇规划准备向郫县方向发展,把沿线村庄划入镇区;邓薇则提出,应沿沙西线向成都方向发展,那边动力更强,土地空间较大。结果建议被采纳,镇总规的发展方向由向南调整为向东。
扎根乡村,乡村规划师用慧心妙手,将乡村装扮得精致而富有人情味。在明月村,记者看到一家农家饭庄,外墙泥着一块原木做框的黑板,用稚嫩的花体字写着三个大字“豆花饭”,“豆”字的上下两笔画成了两个豆角,中间的“口”是一张微笑的嘴巴。下边写着“回锅肉、扎耳根”等菜名。邓小玲说,主人家上小学的小女儿喜欢画画,这是他们特意给孩子设计的黑板。
“以前,在规划院时,成果是纸面的;干乡村规划师,成果是立体的。”邓薇说。
在成都规划界看来,乡村规划师要研究的事情很多,包括投资和经营。一个“花香大道”的乡村规划,设计师被一个问题难住了——种这么多花,维护成本怎么解决,用什么商业模式能实现资金平衡?不能当“花钱的师傅,挣钱的学生”,这也是在城市规划中遇不到的。

进不进城,原来“媳妇做主”
乡村规划不仅是个技术活儿,还要研究社会学。他们描绘出农民进城的标准形象:年龄40以下,初中学历以上,居然还有一个发现:最后进不进城,媳妇做主
张佳说,人往哪里去、钱从哪儿来、地怎么管、产怎么布、形怎么塑,是成都乡村规划要回答的五大问题。尽管成都“小组微生”的村庄那么美,但在城镇化的大潮中,农民去向也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。
在崇州市白头镇五星村,白头镇副镇长易惰告诉记者,白头镇的布局是“一村一中心”,保留一个五星村,做成“小组微生”幸福美丽乡村的典范;其他的“四村一社区”,准备引导百姓住到城镇去,现在,已有70%的农民表示同意。
白头镇离崇州市区只有4公里,与城区是互补关系,周边还有一个重点镇桤泉镇。除了五星村之外,对白头镇其他村的村民,至少有三个选择:进县城,即崇州城区,二是进工业区,三是进场镇。如果是简单的原址重建,就会和产城相融的理念有冲突。
据介绍,成都市有30%的山地、30%的丘陵和40%的平原,全部发展大农业不现实,还是要因地制宜,宜农则农,宜游则游,宜进城就要转移。按照规划,到2025年,成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80%,这样,农民还是要源源不断地转移出来。
现在,成都构建起双核(中心城区、天府新区)、8个卫星城、6个区域中心城市、10个小城市和68个特色镇的市域城镇体系。它们被认为是成都新型城镇化的主战场,大量的空间资源应该是往这些地方聚集。
有专家称,成都现在的特点是“大城市带大郊区”,问题是“大城市过大、中小城市滞后,小城镇过小”。成都市希望,68个特色镇有一定人口密度、经济强度、有完善的功能,发挥辐射带动作用。成都平均下来,一个镇是3000多人,聚集以后,宜从200个镇变成六七十个镇,便于功能完善、配套齐备、三次产业发展。
在成都,乡村规划已经打破了行政边界。成都市邛崃市冉义镇,原来只有700多人,因为离一处占地30平方公里、主营精细化工和家具生产的工业区只有两三公里,成都就选址冉义镇,将冉义和周边4镇70%的农民都转移到这里来,镇上一下子变成了上万人规模。现在,安置房已经基本建好。
为了能打破镇、村的行政界限进行统筹,成都给这一片区取了个名词,叫“农业功能区”。整合后,其他4镇的规模就会减小,只有行政功能,其生产功能就会慢慢萎缩了,或许就成了此后乡镇撤并的对象。
乡村规划不仅是个技术活儿,还要研究社会学。比如为了摸清农民进城的规律,成都进行过农民工进城行为模式研究。发现农民进城分4个阶段:试探、比较、判断、行动,在成都,大部分劳动力是在县域和近县域流动,只有5%左右离开成都。他们的第一选择是进县城、第二是进场镇,进老旧社区,再次是去镇区,是梯度转移,不像之前想象的大进大出。
甚至,他们还分析出影响农民工判断的“十大因素”,包括子女就学、就业方便、亲戚带动等。他们描绘出农民进城的标准形象:年龄40以下,初中学历以上,居然还有一个发现:最后进不进城,媳妇做主。